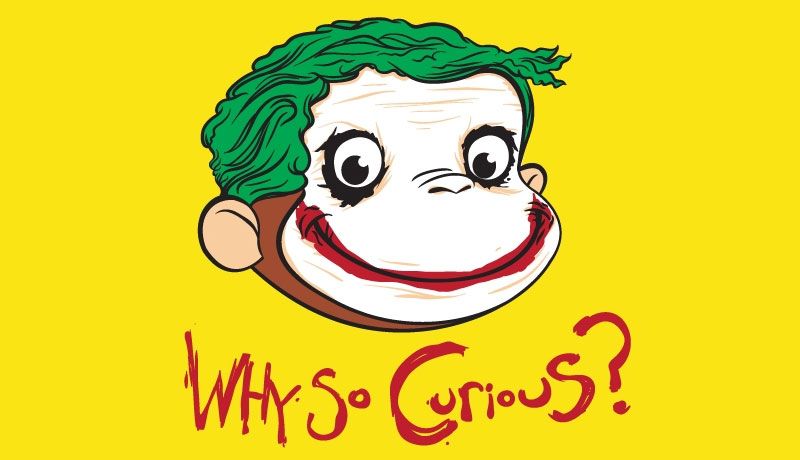誰搬走了我們的半塊芝士: [第二章]第九十二集:世上有一隻怪物叫好奇心
(陳錦波部份)
可能室內說話有點不方便,所以阿花將我拉到與場地同層的一個小型露台,早知有個這樣的地方,剛剛就不用落兩層樓去到那意義不明的大露台,也不用乘那架不知所謂的戇鳩lift了。
出到露台,阿花那原本若無其事的臉立即多了無數冷汗。
她手有點震地取出一個貴得不合理的煙盒,從中取一支,有點徬徨地使用打火機點燃,大口抽幾口,就似是用香煙換走肺裡的烏氣一樣。
良久,她第二支煙抽到一半,看似鎮定了點時,才以激動的語氣質問道:
「Why你不一早同我講自己是M記的員工!?你的職位又是什麼?(普通話)」
我回答:「頭先講過喇,我係經理,落場做野黎講都算係第二第三大。」
她卻搖了搖頭問:
「算了,我最想問是,你為什麼自把自為將這事說給他們知啊?(普通話)」
我卻不像她那樣混亂,作死完之後頭腦居然清晰得匪夷所思。
坦白說,在大難不死後,我的心裡感到一種說不出的愉悅,也許因為做這種仆街野會讓我得到更大的存在感,又或是我已經痴鳩左線。
然後,我滿不在乎地回答:
「可能坐耐左,有D精神錯亂,一時講錯野。但就結果黎講,都唔算係好差姐?」
沒錯,就結果來說,我可是做了一等一對大家都有利的好事,根本就沒有責怪我的理由。
可是,下一秒,她雙目當中流露著萬度高溫卻冷徹地望著我,然後無尾音地說:
「別跟我討論結果是怎樣。(普通話)」
這似是在提醒我,兩人之間的關係與地位是怎樣,要我搞清楚誰是莊,誰是閒;誰是主,誰是從一樣。
她目中無人地望著我的雙眼,開始向我訓話,重新表明自己的原則:
「我所重視的就只有一件事,就是所有事都要在我掌握之內,不論本質是絕對好得像神跡那樣,還是壞得像腥臭的精液都好,我都要它們盡在我掌握之內,明白嗎?(普通話)」
真是個典型的痴線控制狂,但你別以為個個有錢佬都是這個樣子,因為以我所知,其實有錢佬都是人,與普通人一樣,有著不同的性格。
而且從前我所認識的阿花已經是個控制狂,只是變得有錢後,這種性格變得更加鮮明罷了。
她沒有停口的意思,將剛剛所說的話換一個方式再說多次:
「管你帶來了同花順還是四條之類的靚牌都好,怎樣出都是看我的決定,牌局是我的,我愛怎樣打就怎樣打。(普通話)」
要是不扯開話題,她大概還是會繼續重復又重復以上的話,所以我看準時機,大膽打斷她的話:
「係喇,可唔可以具體講清楚……係佢地眼中,M記係一個點樣既存在?點解佢地岩岩既反應會咁古怪既?」
本來正常情況下,她聽到我這樣說或者會破口大罵,大大力屌鳩我,可是她沒有這樣做,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就結果來說,現在我們的情況是利多過弊的,也因此讓我們更加坐在同一條船上,這件事是她知,我也知的。
但對於我作死這件事,她還是極度憤怒的。不過,這只是一時之氣,無奈的發泄罷了,是人之常情。
現在的情況,我很清楚比起沙包,她更需要一個落台階,雖然有錢佬不會在乎這種無謂的禮節,基本上金錢所構成的一身肌肉已使他們比超人更強壯,根本可以隨心所欲。愛怎走就怎走,怎跳就怎跳,沒有人會去阻止,也無人能夠阻止。
不過要是有人提供落台階的話,還是走走無妨的。
我就是清楚這一點才會發出個這樣的問題,陳錦波可以由古惑仔走到今日,成為M記區域經理的路途上是身經百戰,絕不簡單的。
果然如我所料,阿花就像隻位於無風帶的帆船,被我這句像怪風一樣的話吹一把,立即飛快前進,二話不說就直接回答我:
「其實這不是什麼著名的事,沒有緊要到剛入到這個組織就有人告訴你的程度。但大部份人細心觀察過整個組織後,都會有個疑問。這個包羅萬有,名人多得像超級市場的地方,不論是車打食品集團,生果電腦,菱角工業,都市銀行,甚至是可樂公司,你都可以見到當中的成員。(普通話)」
有關共濟會,我也聽過它的事跡,在香港,聽說楊鐵梁,羅便臣和李嘉成等等的著名人物都是其會員實在非常架勢。
來到美國,我其中的人物更加是個個知名,而且更是隨時可以一隻手指將你撳死的級別,像我這種無人無物無靠山的蛋散,要是說錯半句話隨時都有可能灰飛煙滅。
回想起剛剛的行徑,我開始明白有多危險,也感到心寒,更加覺得自己根本係痴鳩線。
但所謂有危就有機,現在得到M記做靠山,至少人生安全是可以確保的。
在我思考的期間,阿花繼續說:
「唯獨是一間,你連它一角影子都見不到。(普通話)」
答案非常明顯,就是我那不得了的靠山:
「M記?」
聽罷她抽口煙,點點頭,冷淡地說:
「沒錯,M記就像一片迷霧,我不敢說是整個共濟會所有人,總之以我所知,大部份人都不太了解它究竟為何那樣神秘,又或是將來會有什麼動向。(普通話)」
我扶一扶眼鏡,開始感覺到一股風暴般的迷團正在蘊釀著,仿佛下一秒就要將我包圍一樣。
阿花則沒什麼表情變化地繼續說:
「雖說是神秘,但對我們來說,這只是單純的『怪事』,所以我們大都是對它重視兩分鐘就把它丟到一角。始終就只是一單怪事,不足以改變世界,沒必要太過在意。但要是有人忽然提起,它還是能重新勾起大部份人的記憶,成為幾分鐘的話題。(普通話)」
聽起來實在完全沒有幹勁,但這也是理所當然,他們日里萬機(就是要考慮每日的時間怎過,怎樣享受美食,扑野,打高爾夫球,為自己的興趣練習之類),對於影響不到自己利益的小事,又怎會有時間操心呢?
不過這樣,只有M記消失,好像不太合理。原理就像是拼圖只缺了一塊那樣,假如缺的不只是一塊,感覺可能會良好一點,所以我就問一問共濟會這幅拼圖的缺塊情況:
「但係全世界有咁多跨國大企業,有一兩個唔入會又有乜咁出奇啊?」
我的問題即時得到答覆:
「確實是這樣,我也曾有過這樣的疑問,可是之後一個前輩解答了這個問題。首先有些大企業真的完全沒有高層入會,不過像M記那樣大規模又沒有入會的,數來數去,其實就只有M記一間,這就是古怪的地方。(普通話)」
聽罷,我非常意外,然後感到自己已經在不知不覺間,太過輕易地進入了迷團的風暴中心,離真相只有一步之遙!
則心跳加速,想著來到美國見過外星人,研究過法輪功,闖過3K黨,殺過人,見過越戰退伍軍人,來到共濟會,終於找到答案了,果然皇天不負有心人!
我吞口口水,滿心期待著問:
「然後呢?佢點講?」
阿花則繼續平淡地解說:
「他說,這裡在座的人們非富則貴,個個都擁有驚人的權力,只要動一下手指頭就能翻雲覆雨,為所欲為,無所不能。(普通話)」
又是沒有意義,everybody know的開場白,但這將會帶我開啟迷團的大門,所以我沉默地忍耐著,繼續聽下去。
「可是這樣的一群人裡面,卻沒有半個人能夠接觸到M記的權力中心,除了知道它是賣漢堡包之外,其他都一無所知。(普通話)」
說到這裡,她手上的煙已經抽完,又換一支,輕輕的點火後,深深抽兩口,微微眨眼再呼出煙圈道:
「也許,我們沒必要與一間快餐店認識得太深,這不值得我們花太大力氣。(普通話)」
我開始感覺到自己已經血脈擴張,心癢得想在胸膛開個傷口入去抓癢,如果化作現實點來說,這一刻,我的心情是:屌你老母!死臭閪!咪鳩再釣我癮,直接講重點啦!仆街!
但我不能這樣做,現在破口一下必會讓阿花不高興,到時就會前功盡廢……屌你老母,我忍我忍我忍我忍我忍我忍我忍我忍我忍我忍我忍我忍我忍我忍我忍我忍我忍我忍我忍我忍我忍我忍我忍我忍我忍我忍我忍我忍……
「可是要了解一個企業,對我們來說根本就只是吹灰之力,而基於作為人類的好奇心,這把灰我們都是很樂意去吹的,但一吹下去才發現,這不是灰,而是一大把黏在金屬上的磁粉。(普通話)」
她沒有望向我,只是望向俱樂部前,湖中的明月,木無表情,機械式向我解說:
「能夠走到今天,來到這裡的,都是明白遊戲規則的人,只是為了毫無回報的好奇心,沒有理由要加大力度去調查。(普通話)」
如果我沒有記錯,這句話我應該之前已經在自己的腦裡面推說過一次,希望一下句不會如我之前的推測。
若不幸是的話,我應該會即時瘋狂屌鳩佢!
然後,她開口了:
「過份的執著是毫無意義的,反正知不知道都不會對生活與生意造成影響,就由它繼續神祕下去吧。(普通話)」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我屌你老母屌你老母屌你老母屌你老母屌你老母屌你老母屌你老母屌你老母屌你老母屌你老母屌你老母屌你老母屌你老母!!
這不是我第一次屌阿花老母!我好記得對上果次已經試過連續屌左佢老母十次,可能是我與她老母實在緣份不淺,又或是阿花這個人實在太摟屌,還是說我自悲心作祟,所以老看她不順眼。
但無論如何,不論誰這樣釣完我癮再爛尾的話,我都會不遺餘力地屌鳩佢。話說雖然我心裡面已經屌到佢兩母女屎眼爆炸,但現實我還是忍住了,沒有即場爆她,反而頭腦清醒地問她一個問題:
「但真係半個有執著想解開迷團既人都無?最後果個前輩知唔知個迷團既真相?」
她居然非常忠實地回答我的問題:
「執著的人當然有啦,就是那個前輩啊,至於迷團的答案呢……(普通話)」
聽到這裡,我的心情就像掘金時以為找到礦脈,卻原來掘到一隻大怪獸的口,被吞進肚子大難不死,愈走愈深,滿懷絕望時卻發現前路有光一樣。
我懷著最大的希望,流露出情不自禁的喜悅,驚奇得像個小孩問:
「結果係……?」
「別管它了。(普通話)」她冷冷地說。
你老母,原來怪獸的屎眼通往溶岩。
不過我依然唔鳩信,有點失控,不知不覺用普通話再問多次:「什麼?(普通話)」
她望著我,緩緩地再次解釋道:
「答案就是這個。他說:『別管它了。』(普通話)」
一時之間我實在唔知講乜鳩好,心裡面就只有一句說話:有無九兩菜啊?
我信鳩到你十足十,聽你鳩嗡聽左咁閪耐,到最後居然比個咁樣既答案我!?我真係有D想打鳩佢。
只可惜,她偏偏就是世上最不可以打的一群人當中的一份子,出了手大概不是被拉去警局那麼簡單了。
至少也應該被捉去拍塞爾維亞電影,真的想一想就打冷震。
當然,見慣世面的我很快就回復冷靜,想出個更好的方法解決現在的困局,是一個突破盲點的問題:
「咁果個前輩今日係唔係度?」
豈料她居然一口就拒絕回答:
「為什麼要告訴你?你可是差點害我墜落困局啊。我警告你以後說話給我先用大腦思考一下先。(普通話)」
說罷阿花將煙頭隨手丟了,準備離開,走了兩步再輕輕回頭,對我作個最後警告:
「同樣的奇跡不會出現兩次。(普通話)」
然後她頭也不回就離開了,只剩下我一人戇鳩鳩地站著。
我無奈地望著那個怎叫也不會回應的背影,心想我根本唔鳩在乎作唔作死既問題,而家我剩係想知M記在共濟會迷團的答案炸!
死八婆!正臭閪!知又唔鳩講我知,係都要釣我癮,點撚解要咁樣對我啊屌你老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