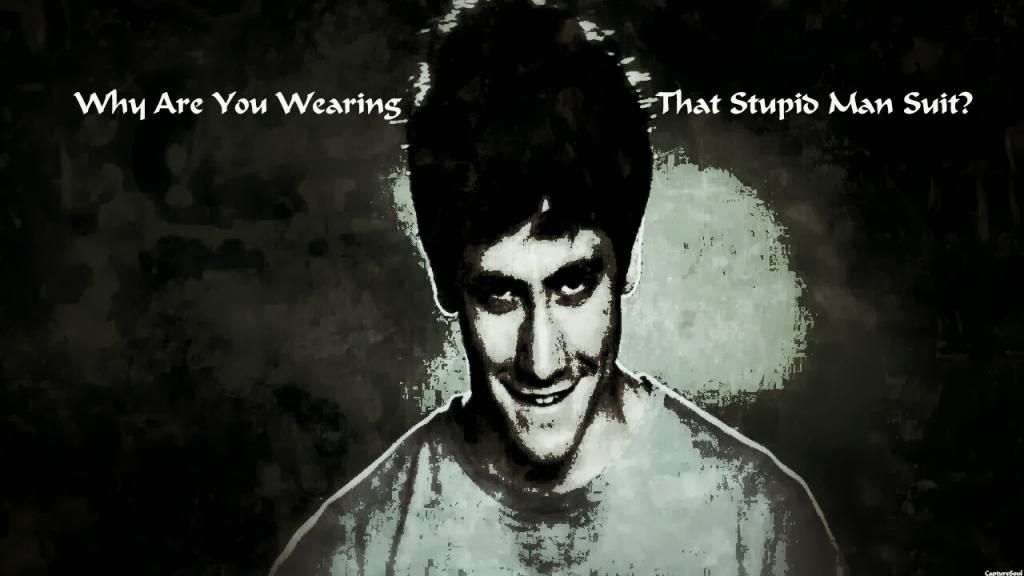誰搬走了我們的半塊芝士: [第二章]第六十集:救世主的服飾
接過四眼仔的電話,我立即致電到總公司,向一個月也見不過兩次的所謂上司申請早退,反正沒什麼緊要的工作,所以馬上就被批准了。
這是我在力奇電訊上班以來首次早退。
這樣做,不是怕了繼續面對超級駭客,也不是為了四眼仔。
其實四眼仔致電給我,只是想問問在他潛水的幾天發生了什麼事,有什麼新計劃?以及巴別塔的Server有沒有遇上什麼意外……種種的問題。
我們在電話被談足足四十五分鐘,當我詳細解釋發生了什麼事以及種種意外後,我才發現,原來這幾日來發生了這麼多的事……我甚至覺得為巴別塔搬家已經是幾個星期前的事,但實際上其實只是發生了不足四日。
明顯地,由調查魚柳包的迷團開始,我空洞的人生就注入了大量的內容,每日都過得充實到匪而所思的地步。
想一想,難道這就是阿熹的生活麼?
這種被他說是沉重的生活讓我每日都有著濃厚的活著感覺!究竟有什麼不好?有什麼痛苦?有什麼沉重?
阿熹為什麼要阻止我去過這種充實而傳奇的人生?又要慫恿身邊的人們做個無知的平凡人,過著每天都千篇一律的機械式生活?
坦白說,對於從前的沒趣生活,我沒有一刻感到幸福,亦沒有一絲留戀。
因為我覺得現在的自己是神。
如果阿熹與我也有著相同感覺的話……那他之前經常擺在口邊的「做個普通人往往係最幸福」,根本就是為了加強自己的優越感而說的!
想到這裡,我心裡面的不滿就像宇宙大爆炸一樣,失控地無限擴張,我已經不知道自己所憤怒的重點是什麼,正如誰都不知宇宙的真理,我都不清楚自己的情緒在搞什麼,只知道種種的負面情緒正在碰撞,膨脹,摩擦,融合,爆發,萎縮,變形,衝擊,溶化,粉碎,焚毀著……
最後,它們聚會成純粹的爆怒,由我的胸膛直衝到頭上,讓我開始有點暈眩的感覺,我坐回轉椅上,摸著頭腦,好讓自己先冷靜一下。
明明只是思考,卻令我的情緒如此失控,究竟發生了什麼事……?
我手肘壓在超級駭客的鍵盤上,托著痛得失控的頭腦,要是繼續沒有好轉的話,我覺得自己說不定真的會死掉。
之後,我失去了意識。
過了一會,我依然托著頭地醒過來,身體的姿勢與失去意識前差不多,所以我推測自己墮到黑暗的時間應該只有一至兩秒。
現在,我的頭痛開始如同退潮一樣消退,再過幾秒甚至連痛楚與暈眩也消失無蹤。
我透過超級駭客那玻璃螢幕的反射看看自己的模樣……我才發現原來自己的長相是這樣既熟悉而陌生。
我有種感覺,好像有點更加地了解自己一樣。
但憤怒的理由,甚至剛剛的情緒是否憤怒……我不知道,往後我也想不透,更在不久之後就忘記了這個問題的存在。
只知道這場深入至潛意識的風暴,將我身體內某個開關打開了。
我放鬆身體,以電腦枱借力,重新站起來。用褲袋內的紙巾抹抹因剛剛失神而流在嘴角至下巴的口水,然後小跳兩下,再像個正常人一樣伸個懶腰,確認身體受控,一切安好,我便背起背包離開那小小的工作室。
由走出貨倉到離開公司的過程中,我沒有望過任何人半眼,像個在草原走路的人一樣,對草滿不在乎,亦無留戀,只是單純地走過。
所以我並不知道超級駭客有沒有注意到我的離去,也不知道死TB有沒有監視著我,總之我就這樣若無其事地離開了力奇電訊,往下一個目的地進發。
剛剛在電話裡,四眼仔約我叫午飯,地點離我所駐分店不遠的一間茶餐廳,一想到要在這個人疫為患的地方,還要跟個男人一邊傾談一邊匆忙地吃飯,腦裡除了「作嘔」兩個字之外,什麼也沒有。
所以我立即就拒絕這個要求,並建議他到大角咀一間小餐館用餐,他馬上就答應,看來應該是取了多日大假去處理什麼事情,而今天正好有空吧。
距離約定時間還有整整兩小時,正好給剛剛快爆炸的頭腦一個休息機會。
我去到豉油街,走過又悶熱而且漫延著汗臭味的隧道,在地底越過彌敦道。一出到地面,經過傳說有死亡病毒的萬年死城——「東京銀座」。
我一眼都沒望過死城,就立即就轉到砵蘭街。
然後我不帶任何特別意圖,專心一致地走,不久已去到朗豪坊。見到商場的其中一個側門,被太陽虐待已久的我當然馬上就進去過一下冷氣癮,好讓自己可以降溫一下。
可是非常不幸,一進到去裡面是一個化妝品售賣區,雖然早有心理準備,但面對著由一陣又一陣又一陣濃烈香水味混為一體的怪味……就像一隻萬年老妖為了遮蓋自己身上惡臭而噴上的香水味……這種異味立即經由鼻腔,無情地直接衝擊大腦,即使早有心理準備也好,還是難免有點輕微的頭暈。
在享受冷氣的同時又要嗅著令人作嘔的所謂香水味,可謂一啖砂糖一啖屎。
我速速離開這個魔窟,然後進到H&X,現在這個時段不太多人但其實還是有人,我在特價區的中年師奶團之中穿插,見她們正暢快地選衣服。心裡實在有點懷疑究竟女人的衣服是不是都是穿完一次即棄?未想到答案,我便從亞皆老街門口出去。
出到去,第一眼見到是一座目的不明的巨型藝術品,因它的形態,我長久以來也稱呼它作「中槍人」。
現在正有個燥底保安在驅趕坐在「中槍人」小腿的大陸遊客,可是驅完左腳,右腳又有人坐,再去軀右腳,左腳又有人去坐,可能因為保安只說廣東話,令遊客聽不明白而引起這種怪異的情況吧。
但也可以是遊客不滿保安在語言上的堅持,而作出的惡作劇。在不同角度看就會有不同的答案,要說到實情是怎樣的話,其實誰都不在乎。
大家都只注重自己所認為的答案,所以這個社會才會亂七八糟。
除了「中槍人」與遊客,歡迎我回歸室外的就只有高高在上的太陽。
我們又見面了,可惡的大火球。
背負著沉重的高溫,我快步向著塘尾道走,不久就找到救星,是一條旋轉形天橋,靠著它的頂蓋,我能夠逃避火球的虐待,並經由此進到又一個冷氣聖域——奧海城三期。
就這樣,我終於離開旺角,來到大角咀的範圍了。
亂走一段時間,我來到一個座落於海邊的公園,雖然在旺角陽光普照,可是這裡卻是烏雲密佈,完全沒有刺眼的陽光。
我上前,雙手撐在分隔地面與大海的中高鐵欄,望著對岸的環境,天空的雲,大海的浪花,我回想起上次來大角咀的原因。是跟一個前度女友在這裡的戲院看電影,至於看什麼電影?
忘記了,又或是根本不想記得。
總之我只記得這裡是我最後一次拖著她的手的地方,因為就在當晚,她以時速一百三十五公里的速度離開我,向另一個地方進發。
而我……今時今日還留在這裡,要我追上一個如此高速的人並非不可能……只是,我已經錯過了那一班車。
事後,我在背後的石椅坐上一整晚,直至清晨才離開,這一夜,我半滴淚都沒有流過。
因為我坐這麼久,是為了讓自己接受一個自己所認為的答案。
而今日舊地重遊,來到這裡,我感受著海風,它依舊拍打著我的面額,可是感覺已經與那一夜不再一樣。
可能是我變了,又或是它變了。
也許,我們都變了。
這是讓我安慰的,因為它告訴我,那一夜已經過去。
至於當中究竟發生了什麼事,我已經不想再提了,往後若有心情才再說吧。
兩年前,坐在這裡的就只是一個剛失戀,隨處可見的頹廢大學生;然而兩年後的今日,他是一個網絡王國的國王,創造主,甚至乎是「神」,手下更有一群得力助手,向社會,企業,國家所隱瞞的各種迷團作出挑戰,而且身邊更有王妃相伴,毫無疑問,是站在高鋒的男人。
講起王妃……我才記得好像忘記了她,馬上就取出IPhone,回頭離開,然後看看她有沒有因為受到冷落而傷心!
走了幾步,在解鎖IPhone前,我垂下雙手,轉頭望著這個地方,深呼吸一口,再看清楚這個地方,我沒說半句話,海風卻不停地吹向我,好像想把我趕走一樣。
我發自內心傻傻地微笑一下,就頭也不回離開這裡。
或者我約四眼仔來這區,甚至乎早退,就是為了來這裡一趟,然後讓我離開,至於為什麼要這樣做?
唉……潛意識這回事,你同我識條春咩!?
「芙(最後上線於今日12:40)
芙:點啊?(11:30)
芙:我果邊d野搞惦完喇(11:30)
芙:岩岩有位婆婆去左(11:40)
芙:明明已經見過幾次依d事,但始終個心都有d up住up住(11:42)
芙:有d師姐話見多d就慣(11:42)
芙:但我覺得始終都係人命……(11:43)
芙:雖然照顧佢地係有d煩,但大家都有傾過計,見過一段時間,點可以慣到嫁?(11:45)
芙:如果我習慣到既話,我覺得自己好冷血囉!(11:45)
芙:但師姐同我講,話如果每去一個就消沉一次會好唔得閒,其實都有道理既。(11:46)
芙:不過我覺得佢地已經有少少唔當d病人係人咁……可能依d就係所謂既專業啦。(11:47)
芙:睇黎我同專業重有一段好大既距離。(11:47)
芙:你覺得點?(12:00)
芙:係唔係好矛盾?(12:04)
芙:如果放底左而家既心態,咁我重係唔係我?(12:10)」
看來在醫院工作,要看破生與死果然是其中一個重大課題,唉……這種問題真叫我有點失去方向,我也不知正確的答案是什麼,即使答,也只會答出「我認為」的答案,沒有意思的。
這種問題的答案,還是讓她自己去追尋好了,始終是個足以影響人生的大問題,如果在這個迷茫期向她植入我的想法,未免太不負責任了。
不過她的話還未說完,我便拉下去,看看這個多口妹還有什麼話說。
「芙:係喇(12:34)
芙:我諗諗下呢……(12:34)
芙:又覺得你唔係煩緊公事喎(12:34)
芙:你應該煩緊其他野,係一d唔想比我知道既野?(12:35)
芙:係唔係同果日黎醫院問我既野有關???? (12:38)
芙:其實你唔想講既話都無所謂嫁 (12:38)
芙:我真係唔介意,唔洗格硬講(12:39)
芙:每個人都有佢既祕密,我明白嫁(12:39)」
看罷我眼定定地呆了兩秒。
坦白說,如果有人告訴我她有超能力的話,我都肯定會深信不疑,這種推測明顯已經超出「直覺」的範疇,是一種遠距離的讀心術!
說不定之前的男友被逼分手的原因並不是在於她的差佬老豆,而是他根本在見家長前已經被芙看破了真心。
我敢肯定,如果她能夠這麼精密地看破我的心情,要看破一個男人是不是為了呃蝦條而接近,根本就是輕而易舉。
在這全能的測謊能力背後還有著一個執法者老豆,就好像有一隊十萬精兵守著的一座靠山而建的城一樣,誰都不能攻破她的城門。
除了本王之外,誰都不能觸碰這門!因為它的出現,就只為向本王而開。
我並不怕她的讀心,因為我的心本來就是屬於她的,沒什麼不可告人!我將會騎著白馬來到門前,讓她歡恩地打開城門。
這就是宿命,是我們兩人的宿命啊!
但我依然有自己的原則,亦不會為她而破壞,除非逼不得已,否則我絕不會向她坦白自己的真正身份。
「有關生死既問題我真係答唔到你,依d問題應該由己自己去搵答案。
至於你問我煩緊乜
我真係煩緊公司野啊,依排有個上司放完假返黎搞到我好多野要做,煩死喇(13:02)」
我又再一次對她說謊。雖然現在襯機向她打聽一下的話,會有機會得知醫院封鎖的線索。
但比起這個迷團,我認為應該將她的安全放在第一位,要是她多口問一下自己上司,而引致什麼不幸意外的話,我將會比死更難受。
而且現在向她打聽這種事,不就是間接告訴她我是個調查員嗎?若知道這一點,她很快就會知道我作為巴別塔創造主的身份。
要行這種百害而無一利的方便,實在不符合我做人的原則。
再者,現在否定一下她的推測,讓她失算,順便質疑一下自己直覺的可信性,對我來說也是一件好事。
看看錶,剛好到了約定的時間,我已經到達奧運地鐵站等待著,四眼仔也非常準時地出現,一見面就開口問:
「南華早報單野你係唔係剩係睇過幅相呢?」
居然問這件事?我有點意外:「下?緊係。」
「咁就岩喇,我班左份正本返黎。」他以一副帶了珍藏咸碟的樣子說道。
這引起了我的好奇心,馬上就想取來一看究竟有什麼特別:
「下?攞黎睇下?」
豈料他居然向拒絕我:「去左開飯先啦,等等坐底再慢慢研究好過。」
雖然聽起來正文的訊息好像與網上流傳的相片可能有所不同,可是見四眼仔的樣子又不像看到有什麼突破,加上我也有點餓了……
就順他意,去餐廳坐下再說吧。